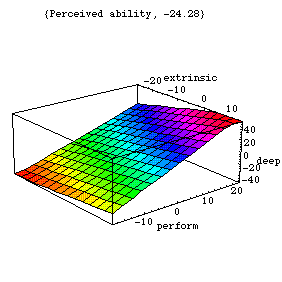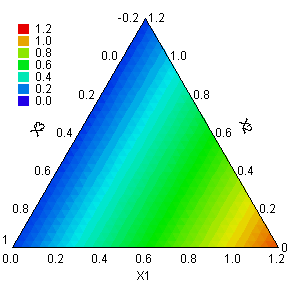方励之·
绝对的转动
经典物理的开山之作“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发表于1687年。书中,牛顿第一个讲到的物理实验是水桶实验。
牛顿说,用一根长的软吊绳提一桶水,把吊绳拧成麻花状。如果你握住吊绳,不让麻花状的绳子松开,桶及桶中的水是相对是静止的,水面是平的。突然放开手,麻花开始放松,吊绳旋转,水桶也随着吊绳旋动。最初,桶中的水并不转动,只有桶在旋转,桶和桶中的水有相对转动。慢慢地,水被桶带动,也开始转动。最后,水和桶一样转动。这时,水和桶之间又是相对静止的,不转动的。但水面却呈凹状,中心低,桶边高。牛顿爵士特别说“ I have experienced”。他亲自做过这实验。
这个实验很容易,任何有水桶和软绳的人都可以试试。我也多次做过这个实验。 1957 冬 - 1958年春, 我在河北省赞皇县南邢郭村下放劳动。天天要用软吊绳的桶从约十米深的井中打水。水桶的姿态只能用软吊绳控制。没有十天半个月的练习,是学不会水桶姿态控制的。结果是,任凭你让吊桶十五次七上八下,每次提上来的水,大多不过是半桶水,而且在旋转。常被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老农(其实不老,同我年龄相仿,但农活经验老道)笑话:“哈哈,半桶知识分子……”。半桶正好作牛顿水桶实验。牛顿爵士当年可能也在苹果树附近的井中打过水,所以,“I have experienced”。
水桶实验的关键是揭露,有两种“桶及桶中的水是相对是静止”的状态。最初(第一状态),绳被放松之前,“桶及桶中的水是相对是静止的,水面是平的”;最后(第二状态),绳被放松一段时间之后,“水和桶之间又是相对静止的”, 水面却是凹状。两种状态中,水和桶之间都是相对静止的,但水面却不同,前者平,后者凹。引起牛顿的疑问,为什麽?
为此,牛顿问一位“聪明人”:“为什麽桶中水面有时平,有时凹?”
聪明人答:“这个问题简单,转动时水面凹,无转动时水面平。”
牛顿反诘:“不对吧。你看水桶实验,在第一和第二状态时,水相对于桶都是无转动的。但水面可以是平的(第一状态),也可以是凹的(第二状态)。”
聪明人觉得这个问题也不难答:“虽然在第二状态水和桶之间相对无转动,但实际上水和桶同时都在转动,它们并不是在真正的无转动状态,只是相对无转动而已。所以,水面是凹的。”
到要害了,牛顿的兴致来了:“那就是说,转动必须分成真正的无转动,和相对的无转动。只在真正的无转动状态,水面才平。有相对无转动,没有真正的无转动,还不行。”
聪明人只能同意了:“应当是吧。”
牛顿再追问:“那,谁是在真正的无转动状态?”
聪明人意识到这是难题,只能碰碰运气了:“水井就没有转动呀!水井就在真正的无转动状态。”
果然被牛顿抓个正着:“哈哈,聪明的朋友,水井建在地球上。如果水井是在真正的无转动状态,地球也应当是在真正的无转动状态。这不就同哥白尼学说矛盾了吗? 地球的自转一天一圈,公转一年一圈,虽然比水桶的旋转慢得多,但也是在转动呀。”
聪明人语塞:“……”
牛顿紧逼:“再想想,什麽东西在真正的(或绝对的)无转动状态?”
聪明人想:是太阳?不对,太阳也有转动。是银河系?(牛顿时代,尚无银河系结构概念)不对,银河也有转动……
聪明人已无招架之功了:“牛先生,还是请你告诉我们答案吧。”
其实,牛顿自己也不知道答案。但是,牛顿的过人之处,在于敢大胆假定他自己也没有见过的东西。牛顿在他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里假定,“绝对空间:其自身特性与一切外在事物无关,处处均匀,永不移动”。“永不移动”的东西当然是不会有转动的。所以,“绝对空间”是在绝对的无转动状态。尽管,谁也没见过“绝对空间”。
这样,水桶实验的一个自洽的解释是,只当桶中水相对于绝对空间无转动时,水面才是平的,否则是凹的。
马赫的解释
一百多年后, E. 马赫 (1838-1916)强烈反对牛顿的解释。主要理由就是,牛顿的假定 —— “当桶中水相对于绝对空间不转动时,水面才是平的”—— 是无法实验检验的,无法证伪的。谁知道如何观测“绝对空间”?
马赫提出的解释是,如果桶中水相对于整个星空背景无转动,水面是平的。当水相对于星空背景有转动时,水面是凹的。马赫的解释中,不需要绝对空间。表面看,马赫似乎只是用“整个星空背景”替代了牛顿的“绝对空间”。但二者有很大不同,马赫的解释是可以检验的。人人都看得见“星空背景”,而看不见“绝对空间”。
人类很早就以星空背景作为位置和方向的基本参考系。无论是在陆地上旅行,或在海上航行,星空背景都是有效的导航者。(南邢郭村是一个很孤立的小村。如果在无月夜去其他村,必须靠星空辨识方向。否则,在四面漆黑的平坦的田野上,很容易走失方向,严重者走成鬼打墙的圈子。所以,老农警告:“阴天夜不出行”。)
表面看,马赫的解释似乎与星空导航相似,实则有很大不同。导航参考系是运动学(位置和方向)问题,而马赫解释赋予星空背景特别的动力学性质。他说,水面之所以变凹,是由于星空背景与水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作用是动力学。马赫还设计了一个“手臂实验”,类似牛顿的水桶,证明他的动力学解释,大意是:
“你站在星空下的一块开阔地。如若你的两个手臂自然地下垂在身体两边,这时你看到的遥远星空(相对于你)必是不转动的。然后,你设法让自己以身体为轴,快速自转。以致你的两个手臂不再自然地下垂,而是向两边分开。这时,你会看到,整个星空(相对于你)在快速地旋转。”所以,用你看到的遥远星空是否旋转,可以区分两种状态“手臂自然地下垂”和“手臂自然地向两边分开”。“手臂自然地向两边分开”是由于旋转星空对手臂的作用。
手臂实验要比牛顿水桶实验还难做。谁能让自己快速自转,以致手臂都不能自然下垂?芭蕾舞演员也难于做到。用芭蕾舞者的裙子在旋转时张开的角度,似可行。
不过,马赫的解释的确可以极精确地验证,无需牛顿的水桶,芭蕾舞者的裙子,而是用陀螺。陀螺的最基本的动力学性质是它具有转动惯性。物体惯性的基本动力学性质是:在没有外界干扰时,动者恒动,静者恒静。转动惯性的基本动力学性质是:在没有外界干扰时,陀螺的转轴方向保持恒定,它的指向是不变的。
按马赫的解释,一个没有外界干扰的陀螺轴的指向,应当相对于星空背景无转动,亦即,
“一旦一个没有外界干扰的陀螺轴指向星空某一方向,它就总是保持这个方向。”
各种飞行器上的惯性导航系统,就是根据陀螺的这个性质。当飞行器转向时,惯性导航仪中的陀螺轴指向相对于星空保持不变。所以,不必看星空背景,只要看陀螺,就可以度量飞行器相对于星空的转动。
再回到牛顿水桶。如果把牛顿水桶和导航陀螺两者放在一起,让陀螺轴垂直于吊绳,按马赫的解释,当水面是平的时,水相对于陀螺轴一定无转动,当水面是凹状时,水面相对于陀螺轴必有转动,这也可以实验验证。至此,在马赫解释里,陀螺,水桶,芭蕾舞旋转,星空背景等之间的关系,都得到自洽的说明,而且有实验支持。
爱因斯坦的“颠覆”
如果“无转动状态决定于星空背景的作用”,那末,逻辑上就不能否认个别星体也会对动力学无转动状态有作用。因为,星空背景是由个别星体构成的。当然,整个星空背景包含大量星体,其作用可能比个别星体的作用大得多。
不过,个别星体的作用是否可以忽略,不能想当然,而应由定量的理论估计。
马赫也意识到,他的解释必须有动力学理论支持。他曾企图建立动力学理论,定量解释“水面之凹,是由于水与星空背景在相对转动时的相互作用”。但不成功。
爱因斯坦于1915年建立广义相对论。
1916 - 1918 年就有人注意到,广义相对论的一个重要推论是,无转动状态不仅取决于星空背景,也决定于个别星体。
如果有一艘飞船飘浮在太空里,它距离所有星球都很远。这时,太空飞船里的导航陀螺轴相对于星空背景是不转动的。如果飞船离一颗星体太近,按照广义相对论,导航陀螺轴相对于星空背景是有转动的。结论是:
“一旦一个没有外界干扰的陀螺轴指向星空某一方向,它就总是保持这个方向”——在星体附近不再正确。陀螺导航的根据被“颠覆”。
“颠覆”效应的大小,取决于星体的质量和转动。如果飞船飞到一个快速转动的大黑洞附近,陀螺轴相对于星空背景会有很强的转动。这时,不能再用它导航。
幸好,地球的质量不大,自转(一天一圈)也慢。“颠覆”效应很小。在近地空间的飞机和卫星,仍可以用陀螺导航,广义相对论只带来极小的修正。修正有两项:
1。测地漂移:地球质量引起的陀螺轴相对于星空背景的转动(1916,W. de Sitter [1]);
2。惯性参考系拖拽:地球转动引起的陀螺轴相对于星空背景的转动(J. Lense 和 H. Thirring [2] )。
在地球上空一千公里以内的导航陀螺,测地漂移大约是每年千分之一度(角度,下同)。惯性参考系拖拽大约是每年十万分之一度。
所以,如果你乘的飞机是Airbus 380 (其中就有由激光陀螺构成的惯性导航系统),那怕飞行一整天(24小时),飞行距离两万公里。测地漂移和惯性参考系拖拽带来目标偏差,分别不大于1米,和1厘米。导弹的飞行时间短,飞行距离小,广义相对论的修正更小。
历时48年的“水桶”实验
今年(2011)五月底,物理评论通讯(Physical Review Letters )发表了一篇短文,只有五页 [3]。它报告了Gravity Probe B 实验的最终结果。Gravity Probe B 实验的目的是精密测量地球附近的测地漂移和惯性参考系拖拽,以定量地检验广义相对论。Gravity Probe B 的主要装置是,一台极精密的陀螺仪放在一颗卫星上。卫星的轨道为圆形,并经过地球南北两极上空,离地高度642公里。它测量陀螺轴相对于星空背景的转动。按广义相对论计算,在这个卫星上陀螺轴的测地漂移和惯性参考系拖拽,分别是每年千分之1.8度,和每年十万分之1.1度。
Gravity Probe B 由斯坦福大学C. W. F. Everitt教授主持 。这项实验历时48年(1963 - 2011)。前45年 (1963 - 2008),由美国宇航局(NASA)支持。它是美国宇航局支持时间最长的一个项目,共耗资 7亿5千万美元,亦即,五页的文章,每页平均耗资1亿5千美元。美国宇航局于2008年停止支持。近三年(2009 - 2011),是由沙特阿拉伯王国的一位王子 —— 在斯坦福大学获PhD 学位 —— 在沙特王国找的钱。
尽管Gravity Probe B耗费的时间和财力巨大,其结果并不理想。按原来宣称的目标,Gravity Probe B 能给出精度达0.01% 的测地漂移数据,和精度达1% 的惯性参考系拖拽数据。而最终结果的精度只分别是 0.28% 和 19%。比预期的精度差十倍以上。 因此,引来不少微词 ,“花钱太多了……”。
不完全成功的主要原因是,项目主持人低估了技术上的困难。技术的关键之一是陀螺的稳定性。我认识Everitt教授,他年纪长我两三岁。80年代初期,Everitt访问过中国。那时Everitt 正雄心勃勃招兵买马,因为项目进入工程阶段,需要工程人员。Everitt曾问我:“你认识不认识搞陀螺的中国工程专家,有好的给我推荐。”我说:“试试看”,我知道七机部里有人研究陀螺技术。但是,Everitt 回美国后不久,就来信说:“不必找了,美国防部不同意找中国陀螺专家,因为陀螺是军事技术, 不能让中国专家介入。”
美国防部的戒令,后来好像废了。Everitt 的团队里,有中国学生。可能因为 ,美国防部认识到,Everitt 要做的陀螺,难有军事应用。Everitt 等在他们的论文中一开始就写到,他们需要的陀螺的稳定性要比现今最好的导航用陀螺高一百万倍!Everitt要测“每年十万分之1.1度”的转动,那末,陀螺的不稳定性至少应当小于每年百万分之1度。而Airbus 380上用的激光陀螺的不稳定性,不会小于每年1度。所以,它比Everitt 等的要求——小于每年百万分之1度,要差一百万倍以上。(物理和天文前沿实验用的仪器,其精度,一般都比民用和军事设备高。许多高精度技术,是物理和天文前沿实验的副产品。)
我在Everitt的实验室看过他的陀螺仪原型。它由4个乒乓球大小的水晶球构成。球的每个方向上不得与理想球面有40个原子厚度以上的偏差。球的表面再镀以鈮。4个水晶球都放在液氦的低温(1.8K)环境里,几乎没有热噪声。在此低温度下,鈮成为超导体,当镀鈮水晶球转动时,会产生磁场。磁场的方向就是陀螺的轴的方向。Gravity Probe B即测量磁场方向相对于背景星的转动。
虽然Gravity Probe B不完全成功,Everitt 等人近半个世纪的努力,仍是功不可没。它是第一次在近地空间,用陀螺直截了当地证伪了“一旦一个没有外界干扰的陀螺的轴指向背景星空某一方向,它就总是保持这个方向”。其结果支持爱因斯坦理论预言的测地漂移和惯性参考系拖拽。
下一轮的“水桶实验”
今年(2011),意大利空间局将发射激光相对论卫星(Laser Relativity Satellite [LARES] )。计划费用为4百万欧元 。其目的是要将惯性参考系拖拽测准到 1% [4]。LARES 不用陀螺仪。LARES 的轨道本身就是一个陀螺。(同行们正在 关心,意大利债务问题是否会影响这个项目)。
等着瞧,四百多年的牛顿水桶,还在转。
参考文献
[1] W. de Sitter , Monthly Notices of the Royal Astronomical Society, 77, 155, (1916)
[2] J. Lense and H. Thirring, Phys. Zeits, 19, 156, (1918)
[3] C. W. F. Everitt et al. Phys. Rev. Lett. 106, 221101, (2011)
[4] I. Ciufolini et al. Space Sci. Rev. 148, 71, (2009)
2011, 9. Tucson
Some theologians claim that Easter is more important. That's wrong. When we celebrate one, we celebrate the other.
By JOHN WILSON One of the hallowed Christmas traditions is the Anti-Christmas Rant. It takes many forms, and anyone reading this newspaper will be familiar with most of them. But unless you routinely hang out with people who argue about theology the way many Americans argue about politics or football, you may not have encountered one variant of the Rant that has been gaining momentum in recent years.It goes like this: Christmas isn't simply bad for all the usual reasons—the grotesque materialism that its celebration encourages, the assault of sentimentality and kitsch that somehow seems to grow worse every year, and the smarmy wrapping of it all in the most inflated spiritual rhetoric. On top of all that, says the Ranter, there is a grievous theological error. In placing so much emphasis on Christmas, Christians fail to grasp the meaning of their own story—in which Easter clearly should take pride of place.This complaint isn't new, but it's been voiced more frequently of late. And not from the fringes, where members of tiny sects patiently explain that Christmas and Easter are pagan holidays that conscientious Christians must boycott. Well-respected voices are making the argument. There's Terry Mattingly of getreligion.org, for one, and N.T. Wright, a former Bishop of Durham in the Church of England. And Rodney Clapp, who presides over Brazos Press, a major Christian publisher.
"I have the cure for the Christmas blues," Mr. Clapp wrote this month in his column for the Christian Century. "It is called Easter. On occasion it takes an outsider to remind us what is central to the Christian faith. So I turn to Rabbi Lawrence Hoffman for a salutary reminder. As Hoffman once wrote . . . 'Historians tell us that Christmas was not always the cultural fulcrum that balances Christian life. There was a time when Christians knew that the paschal mystery of death and resurrection was the center of Christian faith. It was Easter that really mattered, not Christmas.'""The climax of the four Gospels is not Christmas," Mr. Clapp added, "but the events we celebrate as Easter."Where to start with what's wrong with this analysis? Let's begin with Rabbi Hoffman's contention that Christmas never "really mattered." Such hyperbole reveals the false dichotomy at the heart of this particular Anti-Christmas Rant: the idea that Christmas is more important than Easter, or vice versa, and we must choose between them. That's no more cogent than suggesting that Revelatio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Genesis.Christmas brings us face-to-face with the mystery of the Incarnation—the preposterous claim that the creator of the universe sent his son (but how could he have a "son"?) to be born of a virgin (what?), both fully man and fully God: "Christ Jesus, who, though he was in the form of God, did not regard equality with God as something to be exploited, but emptied himself, taking the form of a slave, being born in human likeness," as we read in Paul's letter to the Philippians.This claim we call the Incarnation—and celebrate at Christmas—can't be separated from "the paschal mystery of death and resurrection." The babe in swaddling clothes comes with a mission to fulfill. And as we sing carols for his birth, we see him taken down from the cross, wrapped in "a clean linen cloth," and laid in the tomb of a friend. That's the cloth that is left behind in the empty tomb on Resurrection morning.Easter is implicit in Christmas, and Christmas is implicit in Easter. When we celebrate the one, we celebrate the other, looking forward to the restoration of all things.Mr. Wilson is the editor of Books & Culture, a bimonthly review.
By JOHN WILSON
One of the hallowed Christmas traditions is the Anti-Christmas Rant. It takes many forms, and anyone reading this newspaper will be familiar with most of them. But unless you routinely hang out with people who argue about theology the way many Americans argue about politics or football, you may not have encountered one variant of the Rant that has been gaining momentum in recent years.
It goes like this: Christmas isn't simply bad for all the usual reasons—the grotesque materialism that its celebration encourages, the assault of sentimentality and kitsch that somehow seems to grow worse every year, and the smarmy wrapping of it all in the most inflated spiritual rhetoric.
On top of all that, says the Ranter, there is a grievous theological error. In placing so much emphasis on Christmas, Christians fail to grasp the meaning of their own story—in which Easter clearly should take pride of place.
This complaint isn't new, but it's been voiced more frequently of late. And not from the fringes, where members of tiny sects patiently explain that Christmas and Easter are pagan holidays that conscientious Christians must boycott. Well-respected voices are making the argument.
There's Terry Mattingly of getreligion.org, for one, and N.T. Wright, a former Bishop of Durham in the Church of England. And Rodney Clapp, who presides over Brazos Press, a major Christian publisher.
"I have the cure for the Christmas blues," Mr. Clapp wrote this month in his column for the Christian Century. "It is called Easter. On occasion it takes an outsider to remind us what is central to the Christian faith. So I turn to Rabbi Lawrence Hoffman for a salutary reminder. As Hoffman once wrote . . . 'Historians tell us that Christmas was not always the cultural fulcrum that balances Christian life. There was a time when Christians knew that the paschal mystery of death and resurrection was the center of Christian faith. It was Easter that really mattered, not Christmas.'"
"The climax of the four Gospels is not Christmas," Mr. Clapp added, "but the events we celebrate as Easter."
Where to start with what's wrong with this analysis? Let's begin with Rabbi Hoffman's contention that Christmas never "really mattered." Such hyperbole reveals the false dichotomy at the heart of this particular Anti-Christmas Rant: the idea that Christmas is more important than Easter, or vice versa, and we must choose between them. That's no more cogent than suggesting that Revelatio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Genesis.
Christmas brings us face-to-face with the mystery of the Incarnation—the preposterous claim that the creator of the universe sent his son (but how could he have a "son"?) to be born of a virgin (what?), both fully man and fully God: "Christ Jesus, who, though he was in the form of God, did not regard equality with God as something to be exploited, but emptied himself, taking the form of a slave, being born in human likeness," as we read in Paul's letter to the Philippians.
This claim we call the Incarnation—and celebrate at Christmas—can't be separated from "the paschal mystery of death and resurrection." The babe in swaddling clothes comes with a mission to fulfill. And as we sing carols for his birth, we see him taken down from the cross, wrapped in "a clean linen cloth," and laid in the tomb of a friend. That's the cloth that is left behind in the empty tomb on Resurrection morning.
Easter is implicit in Christmas, and Christmas is implicit in Easter. When we celebrate the one, we celebrate the other, looking forward to the restoration of all things.
Mr. Wilson is the editor of Books & Culture, a bimonthly review.